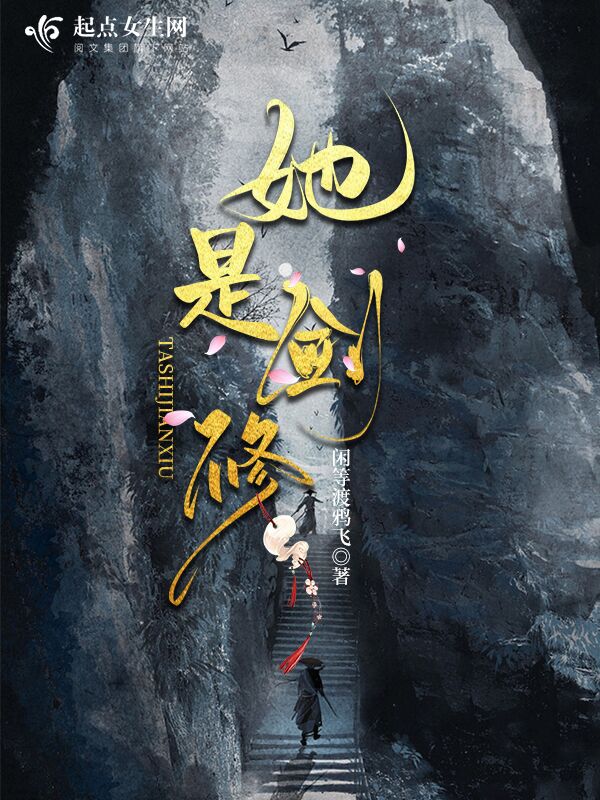分明是一柄长剑,却好似有一伟岸男子凌于空中。
“灵真后辈,你因何故唤我出山?”
赵莼上拜道:“弟子奉掌门之命,取归杀剑回宗。”
那声音骤然停下,久久才言:“崆绝那小子,当年迁宗留我在此,想的是还有回来之机,如今,却是要彻底离去了么?”
崆绝道人,正是当年带领灵真迁宗幽谷时,后执掌灵真的第三代掌门。在此声音口中,却成了“那小子”,不过也不奇怪,断一道人的佩剑,距今怕是有两千余年了,千年前的人物,在他眼中,确也年轻。
“我问你,此是什么时候,门中掌门为何人,因何要带我去幽谷?”
赵莼注意到,他仍是以“去”来形容幽谷,想必对松山,还是颇为眷念的,于是答道:“距迁宗幽谷,已过去近千年,如今乃是第六代掌门途生道人执掌宗门。现掌门有性命之虞,恐壬阳教趁机生事,故特遣弟子前来,取回宗门灵剑。”
“昔日便是它壬阳,截断灵真气运,杀上山门来,如今竟是狼子野心未改,硬要吞下灵真这块肉么!”闻得此话,长剑狂怒不止,剑身震颤,连同松山也随之颤抖。
片刻后,它收去威势,落于赵莼身前:“灵真后辈,我为归杀剑剑灵,亦以此为名,你速速带我回宗,途中将近来宗门之事讲与我听!”
赵莼道一声:“得罪了,归杀前辈。”便握住剑柄,唤出烟舟符箓,立时折返灵真!
此时,灵真派中,亦是一片风雨欲来之势……
“师兄!掌门唤那秋剪影前去了,你怎的不去争上一争?”葛行朝来回踱步,时时叹气,向着李漱不解而问。
李漱却是安坐于椅上,抬眼道:“行朝,我问你,这些年,我为何要与她相争?”
“自是不让长老议事成为她的一言堂,不让你我被排挤至边缘,成个空有名分,而无实权的假长老!”葛行朝疾步回来,坐在李漱身旁,“往后她成了掌门,还有咱们师兄弟什么事?”
“她若不是掌门,谁当是?你我,还是那不问事的吴运章?”
此话问得葛行朝哑口无言,闷闷坐于椅上。
李漱轻拍他的肩膀:“当年师尊仙逝,定下师兄为掌门,你我可有不服?”
“自然没有,掌门师兄天资过人,甚于你我,又以长老身份,代行掌门之责许久,门中上下均是敬服于他……”葛行朝只是性格莽直,却并非愚蠢,此话一出,顿时回过味儿来,天资过人,代行掌门之责,这不正是如今的秋剪影?
“我再问你,秋剪影当了掌门,会杀你我否?”
“她怎么敢!”葛行朝笃定道。
李漱便又问:“那壬阳教攻进来,会杀你我否?”
葛行朝久久无言,听李漱道:“其实你心中也清楚,只是这么多年随我一道,争惯了。”
“然而再怎么糊涂,也要明白,什么该,什么不该……”
李漱年轻时桀骜,除却师兄途生道人与师长的话,谁都不认。但其并非贪欲遮眼之辈,大敌当前,他与秋剪影,谁更合适成就分玄,几乎是显而易见的结果。他虽有所不甘,却也能按下心思,拱手让出机会。
宗门,这个捆缚了师兄几乎一生的枷锁,如今也牢牢套在他身上。
“我们,谁都没能逃过。”他站起身来,向外走去,声音渐渐传入葛行朝耳朵:“此后师兄弟三人,也只剩下你我,稳重些吧。”
葛行朝颓然于座,低声道:“可是,我总觉得,她和掌门师兄不一样。”
……
上严殿外,郑辰清满面凝重,站于秋剪影身后。
他虽是掌门之徒,然而因途生道人寿数将近,时常需闭入关中,不见外人,故而常常是秋剪影授他功法,说是师姐,其实算得上半个师尊。
“如今壬阳教来势汹汹,宗门已是陷入极危之中了。”
秋剪影仿若没听见此话般,怔怔而立。
许久,才听她道:“你可知师尊今年多少岁了?”
“算上今年,不过一百二十整。”她此问,并不为郑辰清所设,仿佛是为自己而设。
“师尊从凝元巅峰,强行破入分玄,折寿两百。便是折寿后,寿数流失数倍快于旁人,也不会十年就要坐化。从接下掌门那一刻起,师尊就没出过上严殿,这铁桶一般的护宗大阵,谁会知晓是由他以生机而续的呢……”
郑辰清又惊又悲,不知如何回话。
而秋剪影,也无要他回应的意思,只是自顾自道:“如若他不是掌门,必然是南域纵横风云的天才。宗门,真就如此重要吗?”
“师姐!”郑辰清见其目光无神,似是入得魔障,忙要出声。
秋剪影步入殿中,目光坚定,忽地顿足道:“从他关上殿门的那一刻起,我就告诉过自己,此生,绝不要如他一般,可怜又愚蠢。”
说罢,大步向内行去,留得脸色大变的郑辰清,细思她此话何意。
内殿内,途生道人盘坐于仙鹤环绕之处,秋剪影神色肃然,知这是护宗大阵阵眼,十年前上代掌门寿尽于此后,算上今日,已是吞去两位分玄的性命了。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