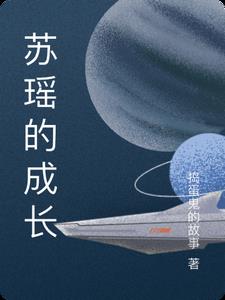他叫牛大宝,农民牛三次的大儿子。
不,他不叫牛大宝。
他是程立,村长程富饶的儿子。
程立没有精神分裂,他有两个身份。每个人都是多面的,他只是比较极致罢了,这并不是奇怪的事情。
程立从小腿上都会系着绳子,被锁在家里,绷直、摔倒、爬起,再绷直、摔倒、爬起。
等着背朝天、面朝黄土的父亲牛三次耕种回家。
他才能够解开绳子,有短暂的自由时间。
五岁那年,他不再被绑在家里,可以在村里上蹿下跳。
他每天都会跑到河边,看程立钓鱼,是程富饶真正的儿子,不是他这个冒牌货。
那个看护的仆人,又钻进了寡妇的门。
半个时辰后,便会系着裤腰带出来。
趁着四下无人,程立走到河边,将程立推进河里。
蹲在地上看着他扑腾着水,人浮上来就用木棍戳下去,慢慢的沉底溺亡。
他坐在那儿,等着仆人回来。
“大宝,见到立哥没。”
春风得意的仆人吹着流氓哨,左右没有见到程立,疑惑的问道。
程立指了指小河。
仆人脸色一变,急慌慌的跌进河里,扎底摸索着。
半晌,他绝望的浮出水面,“完了……”
给了自己一耳光,追悔莫及的道:“让你管不住裤腰带,全完了。”
程立默默递了一句,“村长有眼疾。”
“你…你什么意思。”
仆人霍然从水里起身,趟着河水,两只手像钳子一样抓着程立的手臂。
他抓住最后一根稻草,咆哮的质问道:“是你害了立哥!”
“是你!”
程立唾面自干,看着他不说话。
等仆人疯劲儿缓下来,程立慢吞吞道:“牛大宝死了。”
他惊恐的看着程立,“你、你什么意思?”
惜字如金的程立让他恐惧,畏畏缩缩的跟着回了村长家。
他就守在门外,逢人就说立哥得了风寒,见不得风,不让人见。
傍晚,程富饶来看儿子,屋内只点了一根蜡,他看不清,唤来守门的仆人:“狗剩,进来扶着点。”
“哎。”
腿肚子一软,听到不是要杖杀他,狗剩连滚带爬的进屋,搀着程富饶坐在床边。
他心底发虚,眼睛就乱瞟,这才发觉立哥差了体型。
营养不良,现在太瘦了。
好在,程富饶问了几句,没有去摸,立哥装作迷糊胡乱应了几句。
狗剩听着,语气、停顿竟大差不差。
“愣着干什么。”
程富饶训斥一声,手搭在狗剩手臂上,向外走。
听他吩咐,“明儿,立哥吵闹去河边,也莫要去,等养好了再说。”
“明白,老爷。”
擦了擦冷汗,狗剩虚脱的瘫在地上,他一回头竟看到立哥倚着门框,看着程富饶的背影。
这吓了他一跳,狗剩连忙窜起来,把立哥推进屋内,哭喊道:“立哥,不能出门,让别人瞧见了,就坏事了。”
狗剩守着程立睡觉,他可不敢睡,唯恐哪个不开眼的溜进来。
迷迷糊糊的等到天明,狗剩睁眼一看慌了神,怎么不见了?
热乎着呢。
收回插进被窝里的手,狗剩提拉着鞋就要去找。
转身瞧见,程立吃着糕点,哪儿也没去。
“立哥,糕点哪儿来的?”
程立咽下糕点,道:“丫鬟送来的。”
狗剩一乐,“立哥还知道丫鬟呢。”
见他没理,狗剩语气深长道:“立哥,你要避着人,多长长肉才行。”
程立不置可否,“狗剩,我要去参加牛大宝的葬礼。”
脸被捣烂的尸体,自然只能是牛大宝。
动手的就是狗剩,程立力气小,捞不上来尸体,也做不到。
对上程立无情的脸,狗剩深感无力,妥协道:“我们走小道。”
一口薄棺,已是尽了牛三次一辈子的积蓄,又倒欠了程富饶利滚利。
牛三次没有哭,没有表情,呆呆的看着地面,比纸人还要像纸人。
程立也没有哭,他只看了一眼就走了。
转瞬半年,程立的风寒彻底回转,偶尔出房散步,面也就熟了。
但有人说,立哥变了模样,像牛三次。
一个半月后,牛三次死了,悬梁自尽。
再有一年半载,没有人说立哥像牛三次了,没人记得牛三次。
程立成年,娶了妻,是个黄脸婆,脾气也是蛮横,说打就打,一点情面都不留。
他只能忍着,立哥属于高攀,程富饶临死之前定的婚事。
过了十几年,程立年龄大了,也接受了党国政府的任命。
他就游说村里的遗民,归顺党国、积极参军、保家卫国,来到村尾送军属的书信。
无意瞧见一个妙龄女子,在家中脱去衣裳,露出光滑的后背、圆润的弧度,慢慢坐进浴桶里。
村子里的人,大都还是露天洗澡,趁着晌午人人饭饱觉困,烧好热水,掩着门洗澡。
一个白,一个黄;一个丰腴,一个肥胖。
本小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!